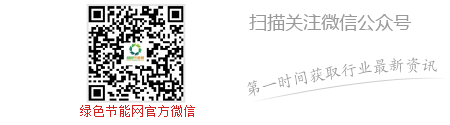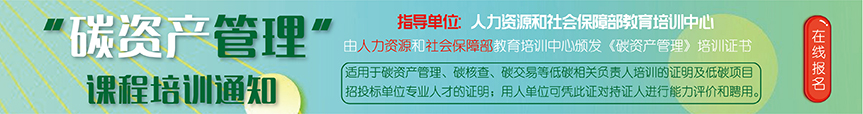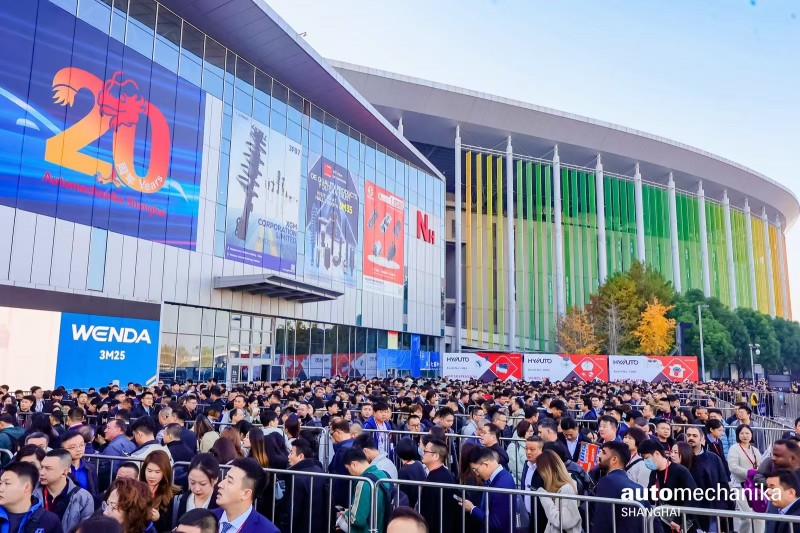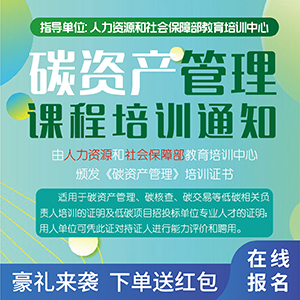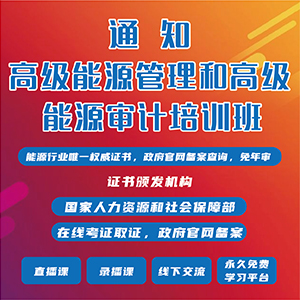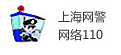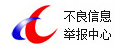強大的英國是用煤炭“燒”出來的
研究空氣污染問題的著作不在少數,如安德森的《潔凈空氣政治》、布雷姆卡姆的《大霧霾:中世紀以來倫敦污染史》、莫斯利的《世界的煙囪:維多利亞時代和愛德華時代曼徹斯特的煙污染史》、雅各布斯的《洛杉磯霧霾啟示錄》等等。這些著作各有千秋,都是從如何治理城市空氣質量的角度展開敘述的,沒有論證城市空氣污染是如何形成的,也未涉足民眾對空氣污染認知的變遷過程。而這恰是彼得·索爾謝姆的落筆重點。
他在第一章“煤炭、煙和歷史”就中擺出了這樣的事實:“當今世界,有三十億人生活在城市中,相當于世界人口的一半,他們中有很多人忍受著不適于呼吸的空氣。”我們生活中很多人抱怨空氣質量如何的糟糕,其實只要生活在大城市,不管你愿不愿意,都要面對空氣受到污染的現實。
越是工業生產起步早的地方,空氣污染的時間也就更早。工業革命發源于英國,很多人以為這都是瓦特發明蒸汽機的功勞。其實蒸汽機并非瓦特的發明創造,他只是改良了這種現代機械。蒸汽機當然是工業革命功臣,但索爾謝姆認為真正引爆工業革命的,是煤炭的大規模開采與使用。煤炭開啟了現代文明,也將地球引入環境污染的時代:“毫不夸張地說,英國之所以崛起成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強大的制造、貿易帝國,都是化石燃料燒出來的。”
英國煤炭資源異常豐富,直到二十世紀初,一直都是歐洲最大的煤炭生產國,年產量2.29億噸。如果僅僅是因為大量煤炭生產,或者蒸汽機的普遍使用,都不足以使英國成為十九世紀空氣污染最嚴重的國家,但兩者結合在一起,就改變了一切。工業革命時期,隨著工廠用蒸汽機取代畜力和水力,各行各業對煤炭需求迅猛上升,作為化石燃料,煤炭在工業文明時代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。一戰前夕,英國煤炭消費量達1.83億噸,一百多萬人在煤礦謀生,參與煤炭運輸、分送以及把煤炭裝填進鍋爐、熔爐、壁爐、廚房灶臺的人也有百萬之多。人們依靠煤炭為工業提供燃料,為鐵路和船只提供動力、保暖和做飯。煤炭也被用于制造煤氣,而煤氣是當時室內和大街上的照明首選。當時有人在報章撰文說:“英國的工業成就有賴于煤炭,而非努力工作和可靠的政府。”
空氣污染治理背后的利益較量
煤炭的燃燒,不僅釋放了可利用的能量,還釋放了大量煙、煙塵、酸性水汽。尤其在煤煙中,會產生毒灰、二氧化硫、溫室氣體二氧化碳。然而工業革命期間,英國人竟認為煤煙是無害的。當時,煤煙彌漫在英國很多城市,民眾對此不以為然。在他們看來,污染并不是來自煤炭等自然資源的使用,而產生于自然生活的過程。他們把疾病的傳播歸咎于瘴氣,而瘴氣是一種不可見的氣體,被認為是腐爛的動植物散發出的。如此一來,哪里發現腐爛生物最多,就認為哪里環境污染最嚴重,沼澤、叢林、墓地、污水坑、下水道是污染之源。
更為荒誕的是,有人不僅以為煤煙無害,而且認為煤煙還可防止污染。在倫敦,由于煤煙日日夜夜不停地排放,整個倫敦在冬季經常遮天蔽日。由于煤煙的無限制排放,肺病、呼吸道系統疾病、佝僂病等伴隨而來,不少人精力衰退,整日咳咳踹踹。科學家和醫生經過實驗,清晰地認識到了煤煙就是健康的主要殺手。
十九世紀末期,英國的公共衛生專家、城市改革者、記者重新定義了煤煙,不再認為它是城市環境可接受的一部分,而將之作為一個城市問題:“人類具有超越以前難以超越的環境限制能力,但又沒有能力預判或控制他們的新技術產生的后果。”對環境惡化的擔憂,當時一些激進的藝術家和作家表現最為激烈。一些人開始懷念工業革命之前的英國鄉村,期望英國徹底放棄工業之路,回歸淳樸的鄉土社會形態。
如比羅斯金、莫里斯等人就認為:在一種被誤導的對物資利益的追求中,英國正在犧牲它與自然、過去的聯系。整個國家都在屈從于城市和工業的需要,鄉村正在失去本來的自然特征。還有學者說對煤煙污染的反思更為強烈:煤煙是一種危險因素,容易導致社會和政治的動蕩。對犯罪、不道德行為、暴民活動來說,因為煙而變得骯臟的空氣提供了理想的掩蓋。當時的歐洲,不僅英國的煤煙排放嚴重,法國也好不到哪里。印象派繪畫大師莫奈在《睡蓮》《日出》等系列油畫作品中,色調中總是煙霧彌漫。他的創作并非另辟蹊徑,而是忠實地再現當時糟糕的空氣。
按照常理,既然全社會都在強烈質疑煙霧的危害性,那么接下來要看如何治理了,但空氣治理并非想象的一帆風順。在民眾的要求下,1912年英國氣象局成立了大氣污染調查委員會,該委員會的目的是對英國各大城市的煙塵沉淀進行科學測量,并抽樣分析空氣質量。然而,對這種類似學術研究的組織,大企業主和資本家并不放在眼里。為了獲取源源不斷的財富,他們并不期望減少煤煙的排放,更不愿意看到企業關門停產。他們把制造煤煙的罪魁禍首推給了城市居民,理由是居民日常生活中使用煤炭所排放的煤煙比工廠更嚴重。英國政府部門在這個問題看法上則在兩面擺動:一面要順應民意,得設法減少煤煙的排放;另一方面又不能與資本家們翻臉,他們是政府部門的繳稅大戶,得罪不起。
金山銀山與青山綠水如何兼得
當空氣污染已影響并威脅到所有人的健康和生存質量時,英國社會的各利益階層都不得不做出相應的妥協。1956年,英國頒布了《清潔空氣法案》,這項法規在空氣污染整治方面起到了“定海神針”的作用。在之后的幾十年中,英國陸續出臺一系列更加嚴格的生態環保法規。在空氣污染、生態環境治理方面,英國人付出了高昂的代價,其他歐洲發達國家也同樣如此。2015年12月18 日,英國關停了最后的煤礦企業——約克郡凱靈利煤礦,這標志著這個工業革命的始祖國徹底終結了煤炭時代。從鼓勵煤炭生產,到控制煤炭使用,到告別煤炭,英國走過了兩百多年路程。
在整治生態環境過程中,不能不直面經濟發展不能停滯、民眾生活質量不能下降的現實。這些年來,為了應對這一難題,英國和歐美各國專注于高新技術和金融經濟的發展,將那些能耗高、污染重的企業,陸續遷移到發展中國家。從另外一個角度看,發展中國家為了經濟快速增長,則是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。有關碳排放控制與減少問題,如今成了國際外交領域的博弈焦點,發達國家總是指責發展中國家破壞了地球生態環境,然而這些發達國家,其實早在兩百多年前的工業革命時,就是生態環境惡化的始作俑者。如何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尋找平衡點,考驗著各國政府的社會治理水平與智慧。
《發明污染》所講述的英國工業革命時期及其后對待煤煙的認識變化、治理空氣污染的剛性策略,對于當前我國生態環境保護有太多思想上的啟迪。我國正處于工業化、城鎮化和信息化發展的關鍵機遇期,不能因為發展經濟和提高生活水準而罔顧日益脆弱的生態環境,可也不能為了生態環境的修復而停止經濟建設。我們既要金山銀山,也要青山綠水。過去三十多年,我們沒有能避開污染后治理的老路,從現在起,我們能走出一條保護環境和社會繁榮兼得的新路嗎?能在新能源新材料技術創新中大所作為嗎?作為當今全球影響力在日益增大的最大發展中國家,世界對我們寄予了創造低能耗高質量生活方式的厚望。